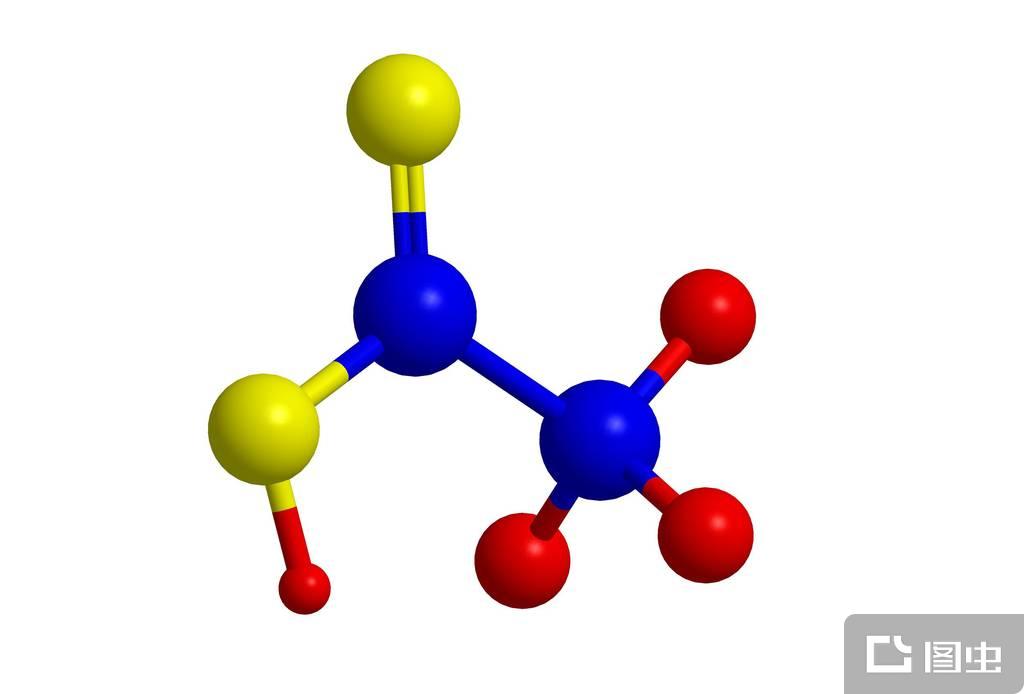流浪汉小说(十六世纪中叶产生的小说流派)

VLoG
次浏览
更新时间:2023-05-20
流浪汉小说
十六世纪中叶产生的小说流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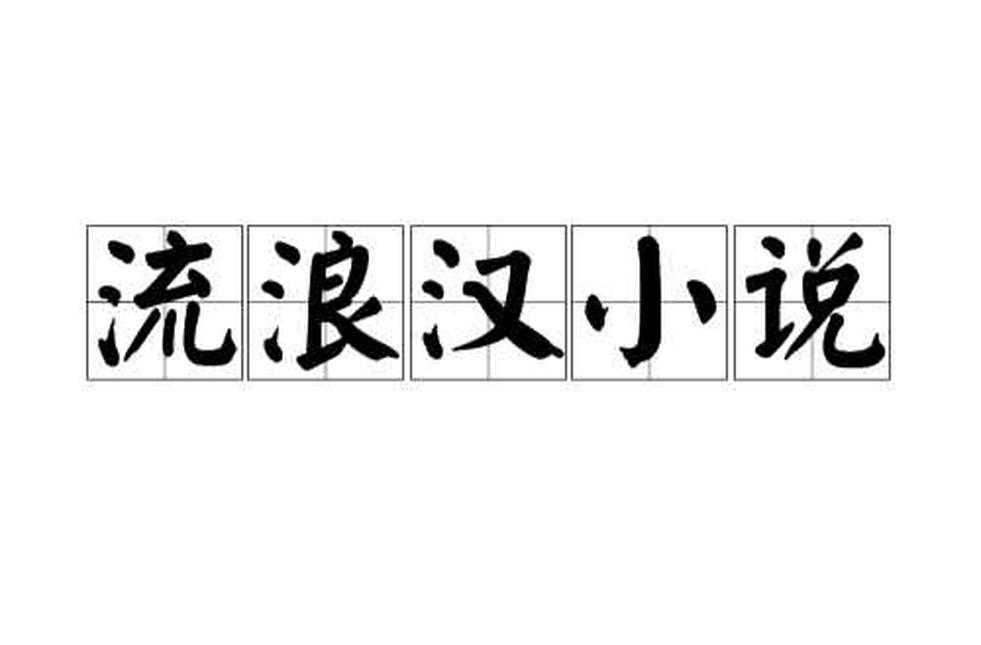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流浪汉小说 |
| 别名 | 饥饿史诗 |
| 代表作品 | |
| 外文名 | La novela picaresca |
简介
流浪汉小说“消极抗议文学”,是16世纪中叶,西班牙文坛上流行着一种独特的小说。这种小说的产生与中世纪的市民文学有关,它以描写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为主,从城市下层人物的角度去观察、分析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用人物流浪史的形式、幽默俏皮的风格、简洁流畅的语言,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它的主人公大多是出身贫寒,有的是孤儿、私生子,童年、少年生活往往不幸,早年一般保持了天真可爱、富于同情心等品格。但当他们一旦脱离家庭、投入社会的怀抱,就感到无法适应,于是为了活命、求得生存,不得不学着去阿谀、钻营、撒谎、诈骗,他们中的不少人终于被社会同化,成为堕落者或狡诈无耻之徒。作品通常在描写他们不幸命运的同时,也写他们为生活所迫而进行的欺骗、偷窃和各种恶作剧,表现了他们的消极反抗情绪。作品借主人公之口,抨击时政,指陈流弊,言语竭尽嘲讽夸张之能事,使读者在忍俊不禁之余,慨叹世道的不平和人生的艰辛。小说中的流浪汉都是动乱社会的特殊产物,他们是在不断解决与周围环境所产生的矛盾中观察社会,认识社会,从而适应社会,求得个人的发展的;他们没有什么明确的道德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常常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在紧要关头,他们往往见机行事,依靠自己的智谋求生存;他们总是以欺骗、偷窃等手段混日子或干些恶作剧,以发泄私愤。所以,这种文学体裁也称为“消极抗议文学”。在题材上,它与中世纪的民间文学有相似之处,以描写城市下层人民生活为中心,并且从城市下层人民的视角观察与分析社会。它往往采取第一人称,以自传的形式描写主人公的所见所闻,以人物流浪史的方式构建小说,用幽默的风格、简洁流畅的语言广泛反映当时人的生活风貌。它较为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但主人公属于性格通常没有发展。比较典型的流浪汉小说——尤其是长篇一般都写出主人公在社会上如何适应、也即由清变浊的过程。
发展
代表作品
特点
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一般采用自传体的形式,以主人公的流浪为线索,人物性格比较突出,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广阔的社会环境描写交织在一起,已初具近代小说的规模。但是主人公的性格没有发展,情节和情节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对于以后欧洲小说的发展,特别在长篇小说的人物描写和结构方法上,有过深远的影响。
它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用下层人民的眼光去观察和讽刺一些社会现象。主人公常是失业者,靠个人机智谋求生存,抵抗压迫。他们没有什么道德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往往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小说和中古市民文学有相通之处。西班牙城市发达较晚,流浪汉小说就是城市发达后的产物。这种小说所反映的正是当时西班牙骑士传奇作家所不屑于反映的生活,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
社会影响
16世纪中叶,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日趋衰微,超尘绝俗的骑士文学和田园传奇在当时的文坛上泛滥成灾。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中,流浪汉小说如异峰突起,它以一种崭新的叙事结构形式,展现出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画幅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物的喜怒哀乐,不仅在当时的作家和读者心海里刮起了一阵阵奇妙的文学旋风,而且给后世文学(特别是欧美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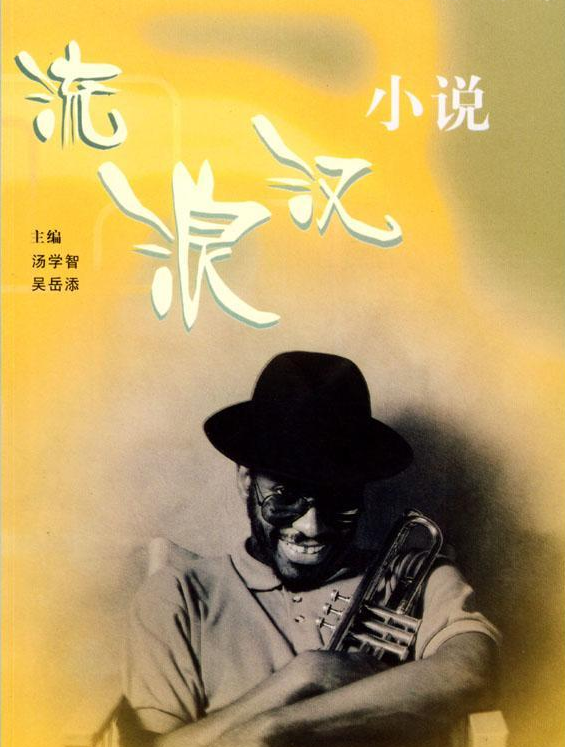
流浪汉小说
正是从picaro这个词的基本含义出发,在外国学术界,有人将流浪汉小说称为“骗子小说”。根据库顿的定义,流浪汉小说是指“以流浪汉为主角的叙事作品。小说通过描述流浪汉的遭遇来讽刺当时的社会。”20世纪以降,由于流浪汉小说的基本特征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体认,这一文学术语常常被用来指称“第一人称叙事体视角、插曲式结构、开放式结尾的描写流浪汉遭遇的叙事作品”。
精神价值
在历代欧美流浪汉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流浪汉形象。欧美学者在研究流浪汉小说时,除了关注小说的叙事方式与结构特征之外,往往还要强调作品中必须有一个真正的流浪汉。例如,美国著名的流浪汉文学研究专家纪昂就坚持这一观点。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流浪汉呢?简而言之,流浪汉最初是西班牙社会上广大的破产者变成的无业游民,他们出身微贱,从童年时代起就尝尽饥寒交迫的苦味。流浪汉没有固定家产和职业,到处受到欺骗和歧视,为了求得生存,只好轮换地给一些主人当佣仆,同时也以狡诈的手段在社会上索取钱财。初出茅庐时,他们往往吃亏上当,后来逐渐学会在尔虞我诈的恶劣环境中欺骗他人。他们对现实不满而又无可奈何,想出人头地而又玩世不恭。虽然偶尔也能发财致富,甚至成为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但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极大的精神代价。无穷无尽的流浪使他们到处都能看到社会的阴暗面,但他们并不想作出积极的反抗,而是采取了以恶抗恶的消极的生存方式。他们的命运浸染着浓重的悲剧色彩,脚下没有一条能够真正通向光明和幸福的路。
从艺术上看,一个典型的流浪汉其实是一个复合型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说,那些频繁出现在欧美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一个小丑、一个流浪诗人、一个无赖、一个土匪、一个浪子、一个小偷、一个暴徒、一个拦路强盗、一个乞丐、一个漂泊者,或者像莎士比亚笔下福斯塔夫式的一个撒谎者、一个吹牛大王、一个好心人、一个懦夫、一个机智的人、一个伪君子、一个道德哲学家、一个喜欢夸张的雄辩家,加上纪昂所说的文艺复兴时代流浪汉的三大先驱——漫游者、穷人与骗子都为最初或后来的流浪汉形象提供了艺术原料。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流浪汉形象,往往融合着上述各种人物形象的艺术基因。
流浪汉是多少带有一些喜剧色彩的悲剧人物形象。他的喜剧性表现在行为方面,而他的悲剧性则表现在命运方面。流浪汉的言语行动常常是机智幽默的,富有喜剧色彩,但在追求理想生活的过程中,由于出身寒微、地位卑贱、力量薄弱,加上他常常采取以恶抗恶的生存方式,所以他忍受了许多屈辱,经历了许多失败。有的流浪汉偶尔或最后在物质生活方面获得了一点胜利,但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那不过是暂时的甚至是虚妄的胜利。小癞子最后依傍圣瓦尔铎的大神父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娶了大神父的女佣为妻,但大家都知道他背负着难以启齿的屈辱(大神父与女佣长期私通),付出了惨重的精神代价;吉尔·布拉斯依靠自己的机智与才干,曾经获得了高位与财富,但他却逐步滑向了堕落的泥淖,到头来还是失去了一切。不过,在整个流浪过程中,流浪汉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和他的坚持不懈的行动,犹如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巨石,带给读者的是极大的美学价值与精神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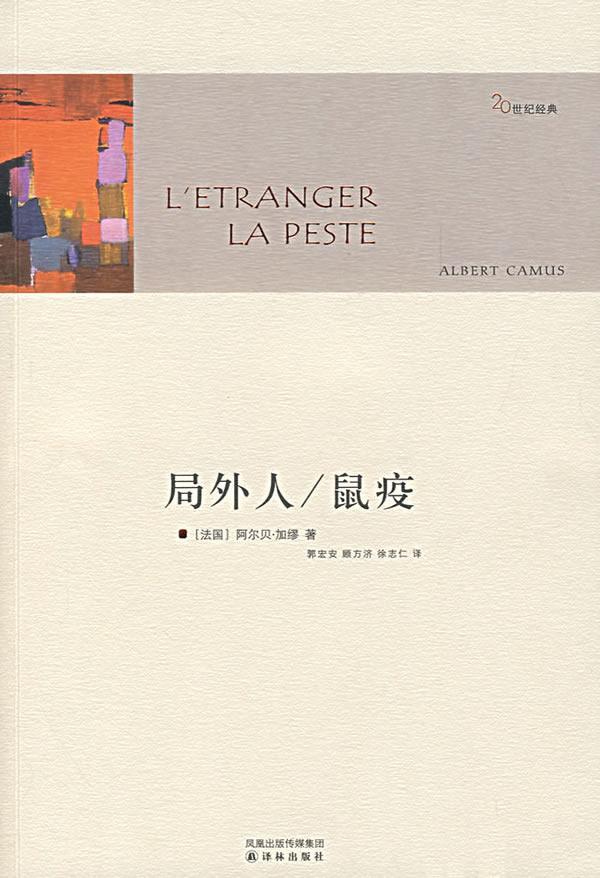
《局外人》封面
在欧美学术界,的确有许多学者都对流浪汉形象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也有一些学者对流浪汉形象的认识是片面、偏颇乃至错误的。就连纪昂这样的流浪汉文学研究大家的观点,常常也是有正有误,有瑜有瑕。例如他指出:“因为流浪汉是一个批评家和一个反叛者,所以他的叛逆态度包含着积极的精神价值。他的格言,正如考狄纳斯所强调的那样,主要是古代犬儒学派门徒的格言:自给自足和独立自主就是幸福状态,为此必须牺牲物质享受、财富、荣誉、地位和爱情。就像流浪汉一样,犬儒学派的门徒对家庭或家乡漠不关心,喜欢采取一种禁欲主义的生存方式。他像反对崇拜偶像并且热衷于现在的无赖一样,依靠经验主义解决自己的生活,从不信奉真理。”在这里,纪昂把流浪汉和古代犬儒学派门徒相提并论,说“流浪汉是一个批评家和一个反叛者,所以他的叛逆态度包含着积极的精神价值”,说流浪汉觉得“自给自足和独立自主就是幸福状态”,并且“依靠经验主义解决自己的生活,从不信奉真理”,这些见解都是中肯的。
然而,纪昂断言流浪汉像犬儒学派的门徒一样,为了自己的信仰“必须牺牲物质享受、财富、荣誉、地位和爱情”,甚至“喜欢采取一种禁欲主义的生存方式”,这样的观点就有失公允,不符合绝大多数流浪汉小说中的实际描写。好在纪昂紧接着又作了这样的补充:“但流浪汉并未坚定不移地遵守这一古代的道德格言。假如他遵守了,那么他的生活就会更加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能完全同意考狄纳斯的看法,他认为田园传奇的主人公和流浪汉小说的主人公同样体现了对邪恶社会的反抗,同样强调了回归自然——16世纪人文主义者的自然主义。依这位批评家之见,流浪汉本该是社会中的自然人,只是被他感到毫无关系的社会群体所束缚。但流浪汉和牧羊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却是截然不同的。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受到迫在眉睫的饥饿的折磨。尽管他后来喜欢表现出哲学家的言谈举止,但他却不得不设法解决眼前的温饱问题……由于这个缘故,流浪汉的行为是自相矛盾的。通过人物反抗社会价值而又追求同样的价值之间摇摆不定的举动,流浪汉小说表达了主人公的这种困境。古代犬儒学派的哲学主要是消极的,除了自由与平静之外,差不多所有的世俗价值都受到流浪汉哲学家的蔑视。”
形象特点
关于流浪汉那种复合型的人格要素,关于流浪汉行为与命运的“西西弗斯节奏”,关于流浪汉那种令人哀伤的“幸福”感及其“局外人”身份,在米勒、威克斯和纪昂等学者的著作中,同样可以看到上述的一些观点。英国学者蒂莫西·G·康普顿把米勒、威克斯和纪昂等人的见解综合在一起,总结出流浪汉形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一个单纯的主人公。纪昂指出:“每一部不折不扣的反映流浪汉生活的小说,都可以用一个单纯的名字来描述。”对于一部堪称真正流浪汉体的作品来说,一个单纯的反英雄的主人公的存在绝对是不可缺少的。
(2)不同寻常的出身。“围绕着流浪汉进入大千世界的环境往往是不同寻常的,因此这些环境成为各种各样的征兆。”有些流浪汉出身于底层社会,他们从不了解母亲的身份,对父亲的身份更是缺乏认识。无论从字面意义上还是从比喻意义上来说,流浪汉差不多总是一个孤儿。他享受不到亲情,所以流浪汉一出生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杂乱无章和动荡不安的生活状态。
(3)狡猾。流浪汉是“一个爱管闲事、蛮横无理、富有弹性、孤苦无依的人物形象,他苦心经营,不过是为了在其杂乱无章的生活场景里苟延残喘,但在人生的枯荣沉浮中,他也能对大千世界采取强有力的防守姿态。”纪昂指出,流浪汉“并非都恶棍化了——骗子总是尽可能依靠他的机智生活,他的狡猾真的算不上什么罪过。诡计与欺骗只是他进攻的武器,而保持一种淡泊的快乐心情,这又是他防御的武器。”不管处境多么艰难,流浪汉总得千方百计地活下去。
(4)千变万化的形态。最典型的流浪汉总是扮演若干不同的角色。他能给一系列主人当佣仆,或者头戴大量职业面具,身穿大量职业服装。“没有流浪汉不会扮演的角色。”就其适应性来讲,流浪汉的个性历来都不好清晰地界定。从悖论上说,在流浪汉逐步变成“平常人”的过程中,他又变成了非人。
(5)疏远。纪昂把流浪汉称之为“半个局外人”。尽管他总是涉足社会,但他从未完全融入社会。在他的生活中,爱与忠诚的缺失导致他跟人和事割裂开来,他变成了米勒的所谓“漂泊不定的一半”。有时,流浪汉似乎快要融入社会了,但西西弗斯节奏又占了上风,于是他发现自己和社会更加疏远了。
(6)内心动荡不安。正因为流浪汉的混沌的出身、千变万化的形态及其和社会的疏远,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他内心的动荡不安。他不能执行自己的决策。也就是说,一时的冲动、好奇心和恶作剧支配着他,使得他遇事不能打定主意,作出决策。
(7)哲理倾向。这一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小说的)叙事立场,同时也来源于流浪汉的好奇心和善于观察的机敏天性。因为流浪汉讲述的是发生后的故事,所以他动不动就用一种哲学的方式对那些经历评头论足。他对社会、政治与人性的洞幽烛微的感想,表明了一种积极而又周到的智慧。
中国状况
吴培显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的“流浪汉小说”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而兴盛。与西方流浪汉小说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作家虽然同样是在关注和反映城市流浪汉的生存或漂泊状态,但作家们并非仅仅停留于“从下层人物的视角去观察、讽刺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层面,也不满足于表现流浪汉们“由清变浊的过程”等,而是在各自不同结构的城市流浪叙事中,敏感捕捉并广角镜般地摄取市场化转型期光怪陆离的城市欲望,倾情关注这些深处都市生活下层、漂泊于城市欲海之中的流浪汉们复杂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揭示他们深层的精神世界及其个性化的人生取向和价值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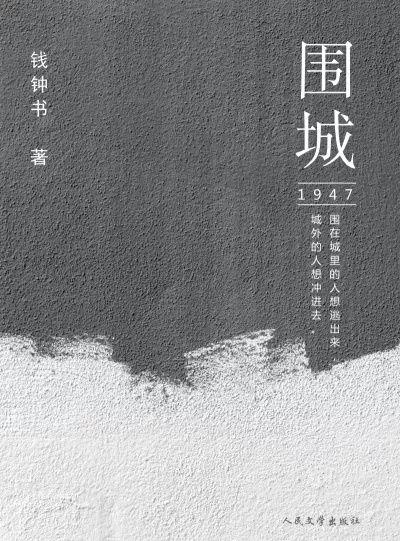
《围城》
在中国,流浪汉小说并没有被过多提及,其实中国的许多著名作家的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可以划分到流浪汉小说的范畴中。
张炜所创作的小说中,“流浪汉”形象的反复出现,以及其深层中对“流浪情结”的“情有独钟”,使得他的小说与西方传统的“流浪汉小说”有了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主要表现在:一、都有一个“流浪汉小说”的框架;二、都有着相似的小说整体的叙事方式;三、都有着基本相似的创作背景;四、各自小说自身的变化脉络也有着暗合——即都由对单纯的现实生活的流浪的描写发展到后来的对因生活骤变导致的思想无着的生活和精神的双重流浪的描写。相似中也有相异,张炜创作“流浪汉小说”的非自觉性,以及他的小说中反映出来的独有的宗教情愫都是他与传统的流浪汉小说不同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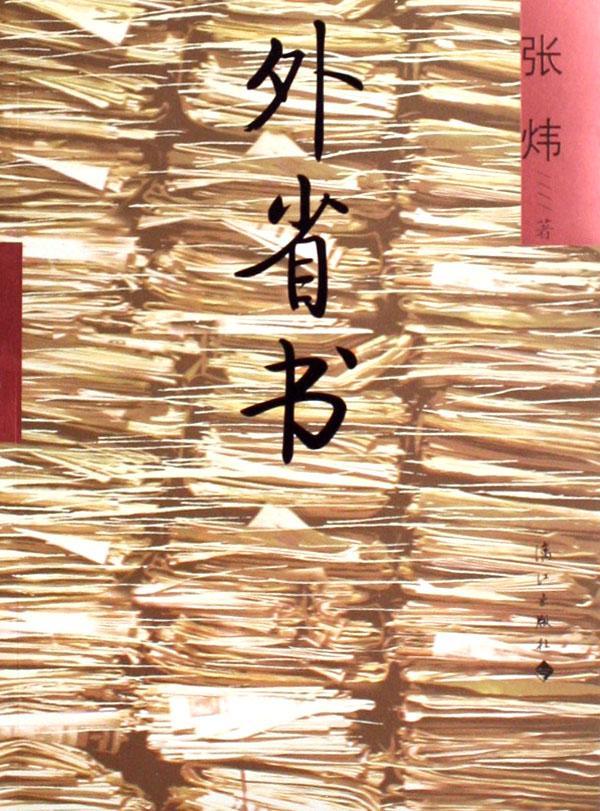
《外省书》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熟知的世界,还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感觉有好多事情要去做,好多路要去走。”“我跟随的是无影无形的一条小路,它没有尽头,但我望得见它,即使眯上双眼也会准确无误地跟定。像被一股奇特的力量所牵引,我的双腿轻捷畅快,背上的行囊也不似从前那样沉重。没有饥饿的折磨,没有困倦的侵扰,说不清走了多久多远......我倾听着藏在心底的呼叫......我在喊:天哪,等等我,我来了”“我在山区和平原、在野地里奔来奔去。一种浑然苍茫的感觉笼罩了我。难以言喻的蓬勃生气、它的独特力量,长久地给我以支持。我认为自己的血液中流动了、保存了它的特质,我现在要做的只是与大地进一步相接相连,让血液中固有的东西变得更浓稠、加快旋动。这样才有可能催生出新嫩的鲜活,从而使陈旧的尽快蜕去。在这个过程中,人会一再地感激领悟到那份真实和永恒,极为厌弃那些虚伪的泡沫,轻视那些过眼云烟......”“人需要一个遥远的光点,像渺渺星斗。我走向它,节衣缩食,收心敛性。愿冥冥中的手为我开启智之门比起我的目标,我追赶的修行,我显得多么卑微。苍白无力,琐屑庸懒,经不住内省。就为了精神上的成长,让诚实和朴素、让那份好德行,永远也不要离我,让勇敢和正义变得愈加具体和清晰。那样,漫长的消磨和无声的侵蚀我也能够陪伴。”
艾芜的《南行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特色的流浪汉小说。《南行记》主要站在现实主义立场,把对流浪人生的体验视为“人生哲学”的命题,以对“自己的生命”的主动把握为特征而进行的创作,显示出了现代流浪汉小说的新发展。因此,这也与西方历史上的流浪小说不同。西方流浪小说中,第一人称“我”都是主人公,小说本身就是“我”的自叙传。这就不免使小说本质上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艾芜的《南行记》中,除了《人生哲学的一课》外,“我”都不是作品的真正主人公,“我”恰似一个别的流浪汉生活的旁观者。在艾芜的流浪汉小说中通常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是围绕小说主人公活动的情节线索,一条是作为观察者的“我”的观察和思维的线索。“我”只是思维的主体,或内在的抒情主体,作品真正的主人公在“我”的眼前活动着,“我”只是观察和思考,却不干扰和左右他们的行为。读者通过“我”的观察和思考认识了故事中的主人公,也通过了“我”的思维活动对故事主人公的精神和行为产生真实的把握和情感的共鸣。如《瞎子客店》中,“我”面对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山洞中的一对瞎子父子,当得知了他们的身世遭际,特别对那一个生下来就没有看见过半点东西,却靠父亲说谎哄他,“说他的眼睛,包医得好,将来定会看得见光明”的儿子,产生了无尽的痛惜与怜悯之心,但“我”无从表达,只能在内心感叹:“老实说,我并不像他父亲那样哄他骗他,我倒真心真意地盼望光明的日子早点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瞎子,生活在黑暗中,只看见丑恶的现象,希望有一天世界光明了,能够看见美好的东西。”这种画龙点睛似的情感抒发在于使读者顿悟作品的象征意义: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光明的人,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得到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