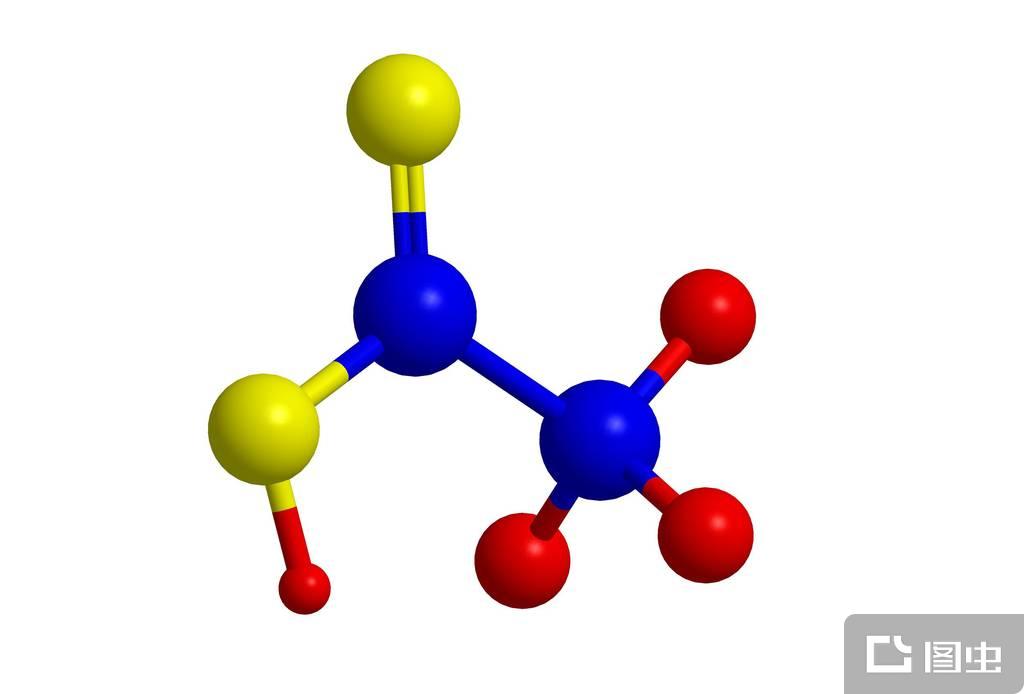陈廷焯(清朝著名词家)

VLoG
次浏览
更新时间:2023-07-24
小编整理:
陈廷焯(1853—1892年),字亦峰,又字伯与,原名世琨,丹徒人,举人,是清朝时期的著名词家。陈廷焯
清朝著名词家

基本信息
人生经历
性情磊落,“与人交,表里洞然。无骩骳之习”。清光绪十七年撰成《白雨斋词话》,生前五易其稿,后由其父陈铁峰审定,删成8卷,光绪二十年由其门人许正诗、王雷夏等刊行。另有《词话》八卷,选《词则》四集二十卷。著《词话》时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卒于光绪十八年(1892)。
词学观点
基本观点
陈廷焯是晚清著名词家,属常州词派后学,其论词上承张惠言余绪,在写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白雨斋词话自序》中,明言自己的创作宗旨是有感于倚声之诗词的六种过失,批评清初自朱彝尊以来“务取秾丽,矜言该博。大雅日非,繁声竞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极”的现实而发,要“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沈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一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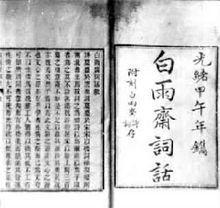
举例分析
此处且引他一段词话如下:所谓沈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难言之苦。又“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又“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皆含深意。此种词,第自写性情,不必求胜人,已成绝响。后人刻意争奇,愈趋愈下。安得一二豪杰之士,与之挽回风气哉!(光绪二十年刻本《白雨斋词话》卷一)
由此论述,可知陈廷焯对中国古典诗词之韵味体会颇深。他的词论在上可直推晚唐五代以来婉约词对他的深刻影响,所谓沉郁就是“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以上诸语,可谓颇得中国古代婉约派词之精髓,自有不可更易之道理。再如他论比兴说:“王碧山咏萤、咏蝉诸篇,低回深婉,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可谓精于比义。”又说:“所谓兴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极虚极活,极沈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绵,都归忠厚。”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这些论述,即便在今天,对于我们深刻了解和体会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要义,仍不失其重要参考价值。但陈氏论词之用意尚不仅在此,他生于晚清末叶传统文化日渐受新学冲击之时代,不要说他的这种崇尚婉约的词风在现实中已不可恢复,即便是自清初以来朱彝尊等人的浙西词派也早已日渐零落,而他却幻想“安得一二豪杰之士,与之挽回风气哉”岂不悲乎!
主要著作
词话体系
《白雨斋词话》共8卷,690余则,是近代词话中篇幅较大的一部重要著作。本书作者自称撰述的宗旨是“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壹是。非好与古人为难,独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为斯诣绵延一线”(《词话自序》),是有意识的针对词坛风尚提出和阐述自成体系的论词主张。

本书基本上持常州派主张,但在一些具体论断上并不拘泥于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周济等的意见。其论词强调“感兴”、“寄托”,认为“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同前),“托喻不深,树义不厚,不足以言兴”(《词话》卷六);突出阐发情意忠厚和风格沉郁,主张“诚能本诸忠厚,而出以沉郁,豪放亦可,婉约亦可”(卷一)。所谓“忠厚”,即词“以温厚和平为本”(卷八);所谓“沉郁”,即措语“以沉郁顿挫为正”(卷八),使之“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卷一)。而比兴寄托、忠厚、沉郁三者是贯串为一的,“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卷二)。同时,强调“入门之始,先辨雅俗”(卷七),力避“俚俗”(卷六)。全书通过具体评论历代词人和词论,较详尽地阐述了上述基本观点。
本书虽然不反对豪放派词,对苏(轼)辛(弃疾)亦有推崇,但过于强调风格沉郁,所以仍以温(庭筠)韦(庄)为宗,称赞温庭筠的〔菩萨蛮〕14章为“古今之极轨”(卷一);韦庄词“最为词中胜境”(卷一);尤其推崇王沂孙,认为“词有碧山(王沂孙),而词乃尊”(卷二)。所以不能认识苏辛词中较直接反映现实的词作的价值。而对民间文学也表现了鄙夷态度,认为“山歌樵唱”,“难登大雅之堂”(卷六)。
陈氏所持的观点主要是常州词派的说法,主张作词贵在“有所感”,“有所寄托”,反对无病呻吟,也反对“一直说去,不留余地”,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对词的评判标准,即“沉郁”和“雅正”。后者易于理解,关于前者,陈廷焯自己解释:“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非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似乎与老杜之“沉郁”有所不同)
在这样观点指导下,与以往正统词评家不同的是,陈氏给予苏辛以及之后数百年的陈维松等“豪放”词人极高的评价:“昔人谓东坡词非正声,此特拘于音调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与之辩也。”“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迦陵(陈维崧)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如此评价可谓难得。
理论局限
然而陈氏所谓“沉郁”字面意义与他自己的解释似乎不并十分吻合,就算吻合,单以风格而言,“沉郁”之标准也有些狭隘。陈氏以此为据,将纳兰性德推出清代一流词人行列,说他“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陈氏以“沉郁”二字框套定论,想是以容若真情流露,不够含蓄为病。此论实在不能令人心服。纳兰性德小词,清新自然,乃真性情之作,“纯以情胜”是其长也,若非如此,纳兰词特色尽失,静安先生(王国维)也不会给他“清新自然,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评价。陈氏词学理论的局限显然是明显的,不过王国维词学与陈氏词学之间的矛盾不能认为是陈的理论的局限性,因为王国维的评价体系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过度推崇“清醒自然”,反对用典,且其词学体系内部存在不少矛盾,因此王国维的理论不能作为理论标尺。同时,陈氏对纳兰性德的总体上的贬低也并非其理论体系的最大的缺陷,甚至不能算是大的缺陷,不能因为与王国维的极端看法抵触就予以放大。
陈氏同以往正统词论家一样,喜欢抬出诗经楚辞压抑民歌俚语。论及北宋词时,他说北宋词“才力较工”而“古意渐远”,又极力贬低柳永说“词人变古,耆卿首作俑也”,当是指其多用俚语,与诗骚不类。即便是他极为推崇的秦观、姜夔、王沂孙,也说“而少游时有俚语,清真白石间亦不免”,显见有些不满。但想来陈氏不会不知诗经中最有价值的国风部分本就是各地民歌,他这种观点不仅迂腐且矛盾了。陈氏另有论宋无名氏《九张机》云:“九张机纯自小雅离骚变出,词自是,已臻绝顶,虽美成白石亦不能为。”然而看九张机笔意笔法,倒像从民歌中脱胎而出,清新自然,活泼灵动,浑不似文人手笔,陈氏此言,不知有何凭据。(若将小雅换为国风,倒还说得通)
在《白雨斋词话》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名字当为“碧山”(指王沂孙),陈氏对于王沂孙的推崇,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词人有此,庶几无憾。”“少游美成,词坛领袖也。所可议者,好作艳语,不鸲地俚尔。故大雅一席,终让碧山。”然而碧山词读来,虽然醇美雅正,哀婉含蓄,但失之纤巧晦涩,有时甚至给人以矫揉造作的感觉。不过陈氏又说:“读碧山词,须息心静气沉吟数过,其味乃出。心粗气浮者,必不许读碧山词。”也许是陈氏心粗气浮吧。
录碧山《南浦》词一首,共品评之,亦作结语。
词作选摘
(一)《蝶恋花·其一》
细雨黄昏人病久,不分伤心,都在春前后。
独上高楼风满袖,春山总被鹃啼瘦。
昨夜重门人静候,料得灯昏,一点悬红豆。
梦里容颜还似旧,南来消息君知否?
(二)《蝶恋花·其二》
采采芙蓉秋已暮,一夜西风,吹折江头树。
赠我明珠还记否?试拨鹍弦,更欲从君诉。
蝶雨梨云浑莫据,梦魂长绕南塘路。
(三)《蝶恋花·其三》
昨日江楼帘乍卷。零乱春愁,柳絮飘千点。
上已湔裙人已远。断魂莫唱苹花怨。
(四)《鹧鸪天》
一夜西风古渡头,红莲落尽使人愁。
无心再续《西洲曲》,有恨还登舴艋舟。
残月堕,晓烟浮,一声欵乃入中流。
幽怀不肯同零落,却向沧波弄素秋。